

返回首页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投稿信箱:1131376436@qq.com 《译龙风云》 |
|
把龙译为 LOONG 及其传播涉及一个民族核心文化安全战略 原标题:影视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翻译 摘要: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有用语的翻译,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真正内涵,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翻译此类词汇,应关注这些特有词汇的异质性和西方人的可接受性。意识形态对译名具有操纵性。应当从意识形态和战略高度认识影视作品的翻译,关注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影视;文化特色;音译;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许多“龙”之类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专属用语,对于其译名在学界仍存有争论。西方所说的“龙”(dragon),代表邪恶。中国龙是祥瑞的化身,应译为“LOONG”。本文仅从翻译和意识形态方面透视此类文化现象。 一、翻译的异质性与可接受性 翻译中的“零翻译”现象由来已久,音译专有名词属此类范畴。“零翻译”就是译者不用译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从深层次看,它包含了源语所有的含义,是最精确的翻译,主要表现在音译和移译上。(邱懋如,2001:26) 例如,电影《花样年华》中“旗袍”就被音译为“qipao”;中国的“关系”有含义相当复杂的人文背景,也用汉语拼音的方式译为“guanxi”;龙由于在异质文化中的“缺项”“空白”或“零对应”,被“异化”为“LOONG”。文化的不可译是有条件的、变化的、动态的。我们有理由预言,“异化”法成就了文化层面上的相对可译性(relative translatability),它将随着多元文化的整合逐渐缩小,借助于解释性翻译,甚至有完全可译的一天,而这一过程则是最大限度地复制并传递源语文化模因(meme)。 孙致礼(2002)指出,当今中国影视翻译的走向已明显偏向以重视差异性为导向的“异化”法,而这种“异化”法对于文化的交流是有益的。对“和而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向往已成为一种世界话语,西方译界就有“延异”之说。(廖七一,2000) 勒菲弗尔和韦努蒂都疾呼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韦努蒂更把奈达的归化策略视为“对外国文本的文化侵吞”,是“不道德的”,提出“阻抗式”(resistancy)翻译策略,拒斥英美民族中心主义的改写,颠覆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其目的就是把观众从认知定势和偏见中解救出来,促进其尊重“他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移情。 因而注重“异”的移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求异”或“趋同”,而应保留、彰显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即“存异”。Dragon 与我们头脑中龙的概念之间存在的出入并不是惟一一个在异族语言里词难达意的现象,这不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一个有着丰富文化蕴涵的字在异族语言里找到绝对对应的词汇,决非易事。两种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不可避免会出现词义空缺和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s)。当然,在出现词义空缺和文化冲突时,如果不了解语言文化编码和隐藏在文化深层的价值取向,随意归化,有时还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杨宪益采用异化法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的“天”译为 Heaven;霍克斯采用归化法译为“God”。在原文的语境中,刘姥姥信的神是佛(Buddha),而不是上帝。杨译没有把刘姥姥念叨的“阿弥陀佛”转化成霍译的“他文化”中的“Thank the Lord for that!”或“God bless you”,而是仿借了梵语“amitabha”的音译“Amida Buddha!”,笔者以为,采用香港的译本中的译法——“O-Mi-To-Fu”或“emituofu”较妥。 |

…… 令人遗憾的是,电视剧《鹿鼎记》(闵福德译为 The Deer and Cauldron)中的这个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鼎”被译者归化为“cauldron”而不是音译为“ding”。(陈刚,2006:4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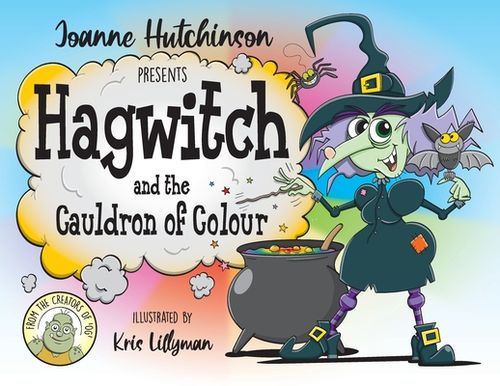
cauldron:大锅
不难看出,采用变通手法,做出种种妥协,迎合了目的语观众,但这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就是遮蔽了来自异域文化“中国的洋味”,造成了源语文化深层结构传递上的偏差、缺损,不利于译入语观众接触和体验异域文化特色。因此,文化意象的传递和翻译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异域文化的互动和移植,既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个性,又不得不考虑勒菲弗尔所说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特别是观众的可接受性对文化传递的影响。正如奈达指出的,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要让观众理解原文的语言文化背景。(谭载喜,1999:29) 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观众,而文化翻译和效应更是不能绕开和游离于观众。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说,翻译的成败只能由观众来校验。精英圈苦于自身所处政治文化语境的囚禁,难免对异质元素涂抹上政治的迷彩,心怀敌意并抵制,完全有可能淡化译文的可达性(availabilty)。 具体到龙的翻译,外国观众不可能以源语观众相同的文化预设和视角审视他们认为值得关注或认为有意义的问题,就会按照自己的“前理解”甚至采用与源语观众冲突的视角去解读,结果可能会产生文化误读和缺损,而他们恰是译品所要影响和“传染”的对象,因而最好在初译时把文化缺省的说明和背景材料即文外补偿或采用解释性翻译进行文化摆渡。 我们不能过度解读“观众反应论”,过分强调观众的接受限度会稀释源语的文化特质。英语的包容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目的语观众存在文化决定的感知定势,我们的关注点应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要异化他们,就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我文化”与“他文化”(otherness)非强迫式的互动机会和界面,使其乐之好之。因此,要厘清是观众“不为也”还是“非不能也”的问题。 通常人们都有“求新”、“求异”的共同心理,但久而久之,最初接触时的梗阻、“休克”逐渐被新异、另类替代,变成习惯和俗成,终将化“隔”为“和”,深入人心。至此,我们可以推测,龙的异化翻译,不是强加于人,它符合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和传播学(communications)原则,具有极大的跨越“张力”和“解压缩”空间。英语已经吸纳了众多的外来词,它也完全可能接受中国的音译词。 从社会思想的流向看,西方社会开始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关注中国的文化诉求,这种“中学西渐”的趋势是一种催化剂,会使西方接受“LOONG”的过程缩短,面扩大,加速“LOONG”式 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以别于中国式英语 —— Chinglish)本土化的进程,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时,不是一味屈就于强势文化,而是理直气壮地腾跃于多元文化的海洋。 |
二、意识形态对译名的操控 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郭建中,2002:162)。无论是《红楼梦》的译介或是《水浒传》不同英译名的处理,无一不受到脱胎于一定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任何阶级都不希望“拿来”与本土文化“撞车”的异域文化,“所谓文化的交流,其背后都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黄天源,2006:39) 这种意识形态包括译者和观众个人的意识形态和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志,即一定的强力人物和权力机构如出版商、强势媒体、奥组委以及一些政党、宗教社团等社会力量的干预以及市场需要,他(它)们会运用各自的话语权对翻译策略、模式及语言进行操纵。 福娃由最初的“friendlies”或“foward”改译为“Fuwa”正是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尤其是赞助人力量的影响,龙未能入选 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也不能不说是赞助人——北京奥组委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民族情感,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每个中国人都有着厚重的龙文化情结。从一些损华翻译的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笔者担心,龙译为“LOONG”是否也会如福娃那样受到来自赞助人——传媒或某些机构的压力,我们不得而知。振兴民族精神,译者负有责任,但更需影视传媒力量推动。 中国要和平崛起,“LOONG 文化”即“和文化”肩负着民族文化原生态传承复兴的重任。除媒体大力宣传外,一些工作需要影视媒体主动去做,去张扬。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面临着式微的尴尬,尚存在巨额“了解逆差”,造成不少西方人对中国误解丛生,也是长期以来中西关系阴霾不散的主要症结之一。龙的重译决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加以讨论,而应视为提升民族文化吸引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影视作品作为“LOONG”文化战略传播的第二战场,一部分内容就是学会中国问题国际表达,传播 LOONG 文化信息,通过一整套龙主题活动传播宣扬(publicize)龙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塑造国家正面形象;另一部分内容则是利用 LOONG 文化、孔子学院等软实力资源,通过多年努力(设立文化基金、对外汉语教学、交换学者、学术会议、开放媒体),使之获得对“中国 LOONG”的新认识,在国际上产生“细雨润物”式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 |

这些作为西方各国“中国问题”专家的汉学家,他们的文化倾向直接影响到西方的“中国政策”以及西方大众的“中国观”,因此抓住并影响了汉学家,使其成为知华、亲华的“院外游说力量”(lobbist),借他们的口传播中国的声音似乎更有说服力,从传教士汉学家与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龙文化扩张”顺应向善的人性核心,终会逐渐吸引和浸染异质文化,并最终获得接受和认同。 中华文明曾在“东学西送”过程中,给西方语言烙上了“Confucianism”和 yin-yang 等汇通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印”。如今,LOONG 这一“原生态”词的诞生将会和 taikonaut(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后西方对中国宇航员的特有称谓)、Fuwa(福娃)、Loongson(龙芯或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芯片)一样演绎出大国崛起的新“神话”,开辟东学西渐的新丝路。中国 LOONG 将不再是和“卧虎”(“crouching tiger”)结伴的“藏龙”(“the hidden dragon”),而是纵横四海“LOONG 头”高扬的“rising LOONG”了。杨、霍两位大师定会欣然在 LOONG 的引领下走出 dragon 的迷雾,译界也会少了一场“四小龙”和“四小虎”的“龙虎斗”,译者更可以免去许多转换意象时的踯躅与无奈。 |

三、并非杞人忧天 影视作品中龙译为“LOONG”不是单纯语言转换的问题,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新译名的影视传播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涉及一个民族核心文化安全战略。一个民族可能会在地域和肉体上被殖民,但只要它的文化没有被殖民,它就仍然是一个闪亮鲜活的民族。杨振宁说:我们应注意注入西方“aggressive”(进取)精神。影视作品翻译应承担起传播龙文化蕴涵的中华民族自强、进取精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邱懋如. 可译性及零翻译 [J]. 中国翻译,2001(01). 2,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走向异化 [J]. 中国翻译,2002(01). 3,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5-59. 4,陈刚. 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5,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9. 6,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62. 7,黄天源. 误译存在的合理性与翻译质量评价 [J]. 中国翻译,2006(04). 作者简介:张煜(1970- ),女,河南信阳人,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 【注】根据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 2021年师资介绍网页,张煜老师为公共英语教研中心副教授(http://wgyxy.xyvtc.edu.cn/info/1025/1066.htm)。 【编后记】张煜老师这篇论文分析阐述了译龙问题深层次的东西。她说得非常好:“影视作品中龙译为‘LOONG’不是单纯语言转换的问题,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新译名的影视传播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涉及一个民族核心文化安全战略。一个民族可能会在地域和肉体上被殖民,但只要它的文化没有被殖民,它就仍然是一个闪亮鲜活的民族。” (黄佶编辑配图,2022年6月29日) 相关链接: -------------------------- (返回顶部) |
返回首页 《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全文免费下载 |